一篇写反了的文章
2025-07-1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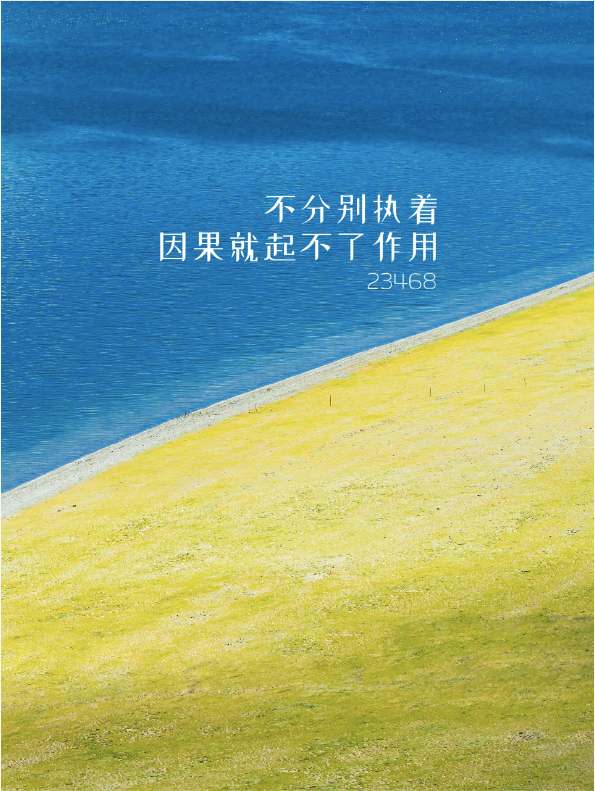
執著於分別心,因果的力量便無從展現,法界也因此閉而不開。
近來靜坐時,心中反覆浮現一句話:「不分別執著,因果才能起作用。」最初聽來,似難理會,後來我才明白,這話不講形式,只講心地。因果本非外在的懲罰與獎賞,而是法界的自然回響,是眾生心念動處所引發的如影隨形之機。但若一心計較,執著是非、善惡、得失,那原本清淨的因緣之流就被自我之網所擋,自然不能開展。於是,我不再追問「這樣做會有什麼果報」,而是反觀那一念起心動念是否真實無妄。
分別執著,是自心在法界面前築起的牆,使萬法不能流通。
許多時候,我們並非無福無慧,而是因執著太深,心量太窄,讓本可生發的因緣被壓縮。譬如一念善心若摻入分別:「這樣做是否能讓我得名聲?」那善心已不純;又如修行時若起妄念:「我是否比他更精進?」那修行已落自我比較之網。這些分別執著,使心念由本來的透明無礙變得渾濁沉重,而法界,作為心念回響的無形體系,便無法與之感應。這便如種子埋入沙中,看似有形,卻終不能發芽。
因果非機械性的對價,而是心念與法界之間微妙而真實的感應。
我曾以為因果如數學,做一事便得一果,行一善即有一報。但這樣的理解,使我修行變得計算,使我行動缺乏真誠。後來我漸漸體悟,真正的因果,是心性自然流動所形成的結果。當我念頭清淨、行止純正,即使不求果報,也會自然與吉祥相應;反之,若心懷目的,即使做出表面善行,也可能因意圖之染而不得善果。這是因為法界感應的,不是行為的外形,而是動念的真實與否。
執著之心無法真正行善,因為它的動力仍根於自我中心的計算。
我們或許可以模仿善行,但若心中仍有執著與分別,那善就帶有條件,非純善。譬如行布施時,如果心裡有「我在給你」的念,那這布施已夾帶高下之見;或是在幫助別人時,若心中已有「你將來要回報我」的想法,那這善念已受污染。真正的善,是心如明鏡,不計較回報、不造作形象,只是自然流出,如泉水滋潤萬物而不自誇。這樣的行為,才是與天心相通的,才能感得真正的因果。
唯有放下分別與執著,心才能真正與天地交感,啟動無礙之法界。
靜夜讀經,讀到「心若無染,則世界清淨」,心中忽然有種無聲的震動。我終於明白,這不是說世界會因此改變,而是我與世界的關係變了。當我不再以自我作為一切的中心,不再處處分別你我、好壞、高低,那我所接觸的每一件事都變得柔軟、開放。我不再用力要求外境改變,而是讓內心先安下來。這樣的心,如同止水,不動則明;這樣的心,也才能感得因果的真實展現。
佛法所引導的「不執著分別」,不是無是非,而是超越自我評判的層次。
有些人誤以為不分別就是無分別,是非不明。其實,真正的「不分別執著」,是指不從自我中心出發去妄加評判,而是從本然的明心處去觀照萬象。我可以知道善惡、分辨是非,但內心不落於自義,也不緣他過。正如老子所言:「知其白,守其黑,為天下式。」真正的清明,不在於否定差異,而是在差異中保持圓融;真正的不執著,是在每一個心念升起時,不為之役、不為之動。
當心與第一義諦相應,則因果即現,法界即顯。
我每日所思所行若能回歸於實相,那些曾經費力追求的結果,反而如水到渠成般來到。這不是因為我有神通,而是因為我開始與那不可言說的真理保持一致。那真理,不在語言文字之中,不在計劃與控制之中,而在每一個不執、不取、不拒的當下之中。當我念頭不再自私,行動不再造作,那看似沉寂無聲的宇宙,便開始回應我,照見我,承接我所播下的一切心念。
法界本無隔閡,只因執著分別而使自己自絕於感應之外。
我常觀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:是否在批判他人?是否在追求名利?是否在暗中比較?這些念頭不一定會馬上生出苦果,但會慢慢在心中築起一道牆,使我愈來愈無法感受到生命原有的澄澈。當我對萬象失去感應時,便會開始懷疑因果不實,甚至懷疑修行無益。其實不是法界無應,而是我心已不感。感者通,不感者閉。閉者,自閉耳。
若一念純淨生起,則因果立現,無需再問何時結果。
我曾問過自己:若我種善,為何不見善果?後來我才懂:真正的善果,往往不是外在的得失,而是我心中那一份無悔、踏實與寧靜。當我無所求地去做一件事,那結果本身早已生於當下。那是一種無形的福氣,會體現在我待人接物的從容、眼神的溫柔、話語的和氣。這些看似無形,卻能深刻改變我與世界的關係。果已在,只是我是否看見它在心中,而非外界。
如夜話,至此。

发表评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