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住在法界大定里
2025-07-1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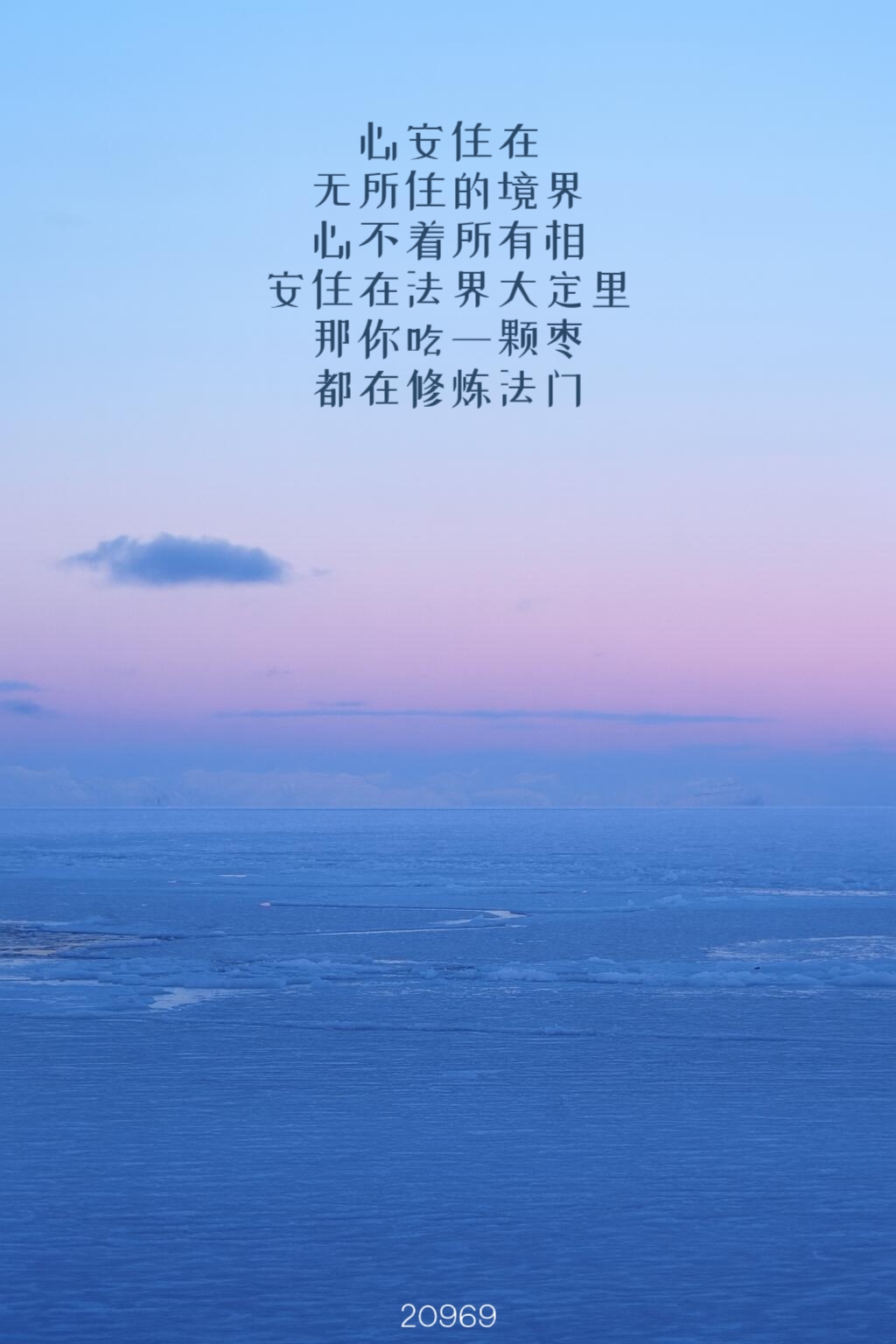
心若能安住於無所住,即一切皆道場。
當我靜坐於黎明前的海岸,天未亮,潮聲如息,寒意微沁,忽然明白:「無所住」不代表無所憑依,而是心不再尋找外物作根,反而因此安住於更深的根中——那是心體本然的安然,是天機自然的回歸。當這份安住出現,一切環境無不成為道場:雪落是法,風起是教,連晨間的一口茶、一粒飯,也能滋養靈明本性。這不是一種刻意修行,而是一種全然的生活態度,是身在俗世,心在法界。
無所住,是對萬象不拒、不取、不著的自在。
心若總想「住」於某處,便如雲想依山,風想栖樹,終究不是它本來的方向。世間萬象皆無常,住於其中,便隨其而轉,無有定處。我曾在困惑中尋找一種可以永恆依靠的力量,遍求於人事物,最後才懂,真正能住的,是心的「無所住」。不被過去牽、不為未來縛,當下即安。這樣的心,處處皆歸,步步為道,不懼起落,不畏變化。因為它不是住在某一事物上,而是住在本體的空寂中。
心不著相,才能見萬相真如。
世人多迷於相——迷於成敗、得失、是非、愛憎。我亦曾如此。然後我漸漸發現,這些表象如雲霧,遮蔽了本有的心光。當我學會不著相,才看見萬相皆實相。原來相不是問題,著才是問題。就像水映月,不著於影,則影清明;若一心執影為月,則失其本。心不著相,不是心無感情,而是心能透過情見本真;不是無所作為,而是不為作為所擒。這樣的心,看花開知緣,看花落知空,一念起,明鏡亦照,萬象俱寂。
大定非死寂,而是靈明不動的全然活著。
曾有人問我,定是否意味著隔絕世界?我說,定者,不動於外,卻無所不感於內。真正的大定,不是昏沉不覺,也不是排斥外境,而是在塵中見淨,在動中見靜。當我於繁忙中學會內觀,心如靜湖,外事如雲過湖面,動而不亂,來而不擾。這種定,不是坐在山洞裡才有,而是在街市中、在眾聲喧嘩裡亦能存在。定,是心體的如如不動,是天心的深藏不露。它不是一種狀態,而是一種能力——讓一切經驗都回歸當下,照見自性。
修行不在別處,便在此刻的一舉一動中。
當我讀到「你吃一顆棗,也是在修煉法門」時,心中一震。這話不華麗,卻極深。世人常把修行看作是進山閉關,是誦經禪坐,但若心仍執著於「修行相」,便未離相。真正的修行,是在一念、一舉、一食、一眠中安住法界。吃一粒棗時,若全心全意,念念分明,那便是修;掃地、洗碗、與人微笑、忍一口氣,皆可為道。修行不過是把日常活出心體,把一切瑣碎之事變為光明之路。
法界不在他方,而是你我當下所在之處。
人們總以為法界高遠,需經年修證方可抵達。我卻越來越深信:法界之門,從未關閉。它不在經書中,也不在寺院裡,而在我們此刻的每一念心,每一處眼光所及。當心不再造作,不再為自己安排戲碼,不再為他人演出角色,那時即是法界顯現之時。法界即是真如之境,是天地萬法之歸,是不二、不別、不可說而明自明之處。這樣的法界,不與人爭,不與事敵,它是慈悲中見勇,是空性中見圓滿。
一切修煉,皆為歸真,而真即是常常不離當下。
若問修行終極為何?我想,是為了回到最本初那顆無染之心。那顆心,不造作,不誇飾,如嬰兒之純,如初月之明。當心住於無所住時,它不被欲望染,不為恐懼動,不被自我所縛。這不是退縮或冷漠,而是從更高的視角看見生命的整體性,看見萬事萬物皆有其來去,皆有其和諧。修煉,不是為了成佛成聖,而是為了不再迷失自己。
即便一瞬之念,也能是道之顯現。
當心安住無所住之境,哪怕只是一念,也能展現道的全體。一顆棗的滋味中有天地之氣,一杯水的澄澈中有法界之靜。修煉,不在於追求什麼境界,而在於體認萬法本自一體,當下即是本體。如王陽明所言:「聖人之道,吾性自足。」不需外求,不需假借,只需從當下一念開始安住,便已步入大道。這種修煉不誇張、不聲張,但它使人深沉,使人光明,使人自在無畏。
心體若圓明,天地萬象皆為教法。
當我心中真正生出這份安住,我便發現:一切所見,皆為法門;一切經歷,皆為修持。疾苦能教我慈悲,喜樂能引我反觀,煩惱能助我知空,寂靜能養我慧命。這世界,不是敵人,也不是外物,而是自己本性的映照。當我們看見萬法皆為自心所現,就會停止責怪,開始感謝。這不是盲目的讚美,而是智慧的明見,是天機之透,是心體與天地合一之所感。
如夜話,至此。

发表评论: